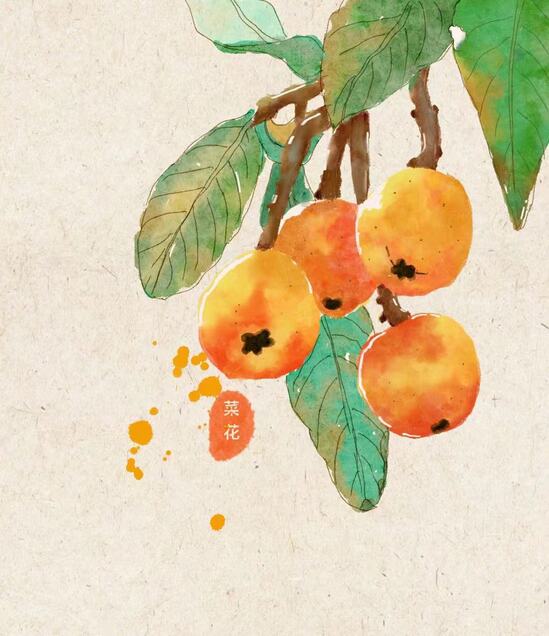|
|||||
|
|||||
|
初夏的风裹挟着微热的阳光,街边的摊位上堆满了金黄的枇杷,一颗颗饱满圆润,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。我站在摊位前,看着摊主们熟练地吆喝、称重、装袋,思绪却不知不觉飘远了。 这个时候,我本该在老家那棵老枇杷树上,像只猴子一样灵活地攀爬,摘下一颗又一颗酸甜的果子,直到肚子鼓胀,门牙被酸得发软,才心满意足地滑下树干。 枇杷是乡愁的引子。余光中曾说:“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,我在这头,母亲在那头。”而对我而言,乡愁是一颗熟透的枇杷,舌尖的酸甜是记忆的开关,轻轻一咬,童年的画面便汹涌而来。刚毕业那几年,我像一只挣脱牢笼的鸟,迫不及待地飞向城市的高楼大厦。地铁呼啸而过,霓虹灯闪烁不停,商场里人潮涌动,一切都新鲜而刺激。那时候,我从未想过回家,甚至觉得那个被群山环绕的小村庄太过闭塞——泥泞的山路、斑驳的老屋、需要徒步走完的九年义务教育,似乎都成了落后的象征。 可如今,年过三十,心境却悄然变化。城市的繁华依旧,可心底总有一块地方空落落的。外面的枇杷再大再甜,总觉得少了点什么;空气再清新,也比不上雨后山间的草木香;夜晚的灯光再璀璨,也照不出老家那片星空的敞亮。有时甚至荒谬地想,连城里的蚊子都不如老家的积极——它们叮人时总带着几分犹豫,不像家乡的蚊子,一见面就热情地扑上来,毫不客气。 为了驱散这种莫名的失落感,趁着五一假期,我回了趟家,我觉得,回家,是治愈乡愁的唯一解药。推开院门的那一刻,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——水泥板弥留的热气、枇杷树的清香、灶台上柴火饭的焦香,混合成一种独有的“家的味道”。父亲掌着勺,见我回来,咧着嘴笑着说了一句:“枇杷熟了,自己去摘。” 隔日清晨,我踩着露水爬上枇杷树,摘下一捧还带着晨露的果子。和父亲排排坐在客厅,一边剥着枇杷,一边看着那台老旧的电视,显示屏还闪着雪花,但谁也没在意。门口传来奶奶喂鸡的“咕咕”声,偶尔夹杂着几声犬吠。那一刻,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:在家里养老,似乎也不错。 乡村的家,有一种让人心安的力量。它不喧嚣,不浮躁,时间在这里仿佛被拉长,每一刻都值得细细品味。城市的“诗和远方”再美,终究抵不过家乡的一碗热饭、一棵老树、一声乡音。老舍在《想北平》里写道:“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,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。”家乡于我,亦是如此。它不是某个具体的场景,而是渗透在血液里的记忆——是枇杷树的荫凉,是夏夜的萤火虫,是清晨的鸡鸣,是傍晚的炊烟。 如今的我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渴望逃离,反而开始珍惜每一次回家的机会。或许,人终究会走向回归,就像枇杷熟了会落地,游子累了会思乡。外面的世界再精彩,也比不上家里那一方小小的天地,让人踏实、安宁。家里的枇杷熟了,身体里的乡愁动了。从此,诗和远方,便是家乡。 |
|||||
|
【打印】
【关闭】
|
|||||
|
|